官员吃西餐 法律竟是文化?萨维尼和格罗斯菲尔德带你颠覆认知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在《论立法和法理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有如下论述:
法律有其特定的特性,如同语言、行为方式、社会基本组织等,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而且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的、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倾向,呈现出独特的景观。
基于这句名言,我们可以理解,法律作为特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当代比较法专家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甚至直言:“法律即文化,文化即法律。”4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法律时,无论从制度还是意识的角度,都要关注其与其他社会文化部分的联系。正如梁志平研究员所倡导的,“用法律解释文化,用文化解释法律”。
孟子说:食色性,人之常情。在讨论某一民族的文化时,必须关注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饮食文化。首先,饮食文化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产生的同步过程,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研究素材。其次,饮食文化与民族每个成员的生理、心理成长息息相关,是形成其他一切文化的基础。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在饮食习惯的源头中找到答案。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在大多数社会中,饮食不仅是一种吸收营养的消化运动,而且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文学等人文关怀已经与饮食直接挂钩。
让我们回到法律的讨论。当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法哲学在城邦奴隶制的摇篮中孕育时,中国的儒家经典中却在宣扬“以德治国、以礼制人”的法律理念。从此,东西方的法律理念便一左一右,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造物主赋予了每个民族同样的发展潜能(就大脑结构和反应方式而言,因为思维是历史发展中人最基本的能力),那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不同呢?正如第一段所倡导的,我们要从文化中寻找答案。饮食文化由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法律理念的形成。我们在研究中西比较法律文化时,不妨引入饮食文化的视角,来思考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法律理念之间的联系。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中国人饮酒时有句老话:关系深,一饮而尽;关系浅,舔舔舔。如果说话人在餐桌上说这句话,无论关系多亲密,关系多深,对方多半也会一饮而尽。于是关系就被考验了,大家融洽相处,餐桌上的气氛不断被推向高潮。中国的宴会就像一个大瓦锅,各种各样的人都放进去,慢慢煮在一起,炖成一味。中国人受的是熟人文化的教育,宴会这样的社交活动,不能容忍没有充分交流的“陌生人环境”的存在。事实上,婚礼、葬礼、长辈生日、孩子一周岁等场合的宴会,为亲朋好友提供了一个相聚、重新认识新建立的关系、巩固旧关系的机会。 于是借助酒精和各类桌游,一个理想的“熟人环境”出现了,一个以感情为纽带的交流平台被打造出来。
既然我们处在熟人社会,那么社会关系的处理就离不开这样一个前提:人不被看作个体,而始终是特定群体的成员。中国人的饭桌上,每个人的座位都要严格按照其在家庭特定群体中的不同身份来安排。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对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我们先来看《红楼梦》第四十回“太君施氏两宴大观园,金元阳三告牙膏令”中荣国府宴请刘嬷嬷的场景:
上头两张榻、四张桌子是贾母和薛姨妈的,下头一椅两桌是王夫人的,其余各一椅一桌。东头是刘姥姥,刘姥姥下面是王夫人。西头是史湘云,依次是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最后是宝玉。李婉和凤姐的桌子摆在三层门槛里面,两层纱厨外面。

座位安排完全以辈分、主客、血缘等身份关系为依据,堪称身份社会的研究典范。文章只提到有资格坐在桌边喝酒的人,并未提及被排除在桌外的人。儿童、小妾、仆人一般被排除在外。作者也是在一个“大家庭”7中长大的。作者的祖父母、叔父、同龄人经常住在同一屋檐下。作者直到中学时期才被允许在餐桌上吃饭。在此之前,一直都是长辈们端起饭菜在旁边吃,几个表兄弟也是这样。在西方,儿童、家庭教师、保姆甚至仆人都可能与成年主人同桌用餐。
在这种中国式的“熟人社会”和“身份社会”中,大家相互认识,易于交流。因此,法律的泛泛指导不仅不能发挥其效率特性,而且可能因其抽象性而缺乏“实质正义”。而且,一旦发生纠纷,人们最渴望的是“得到一个解释”,而如果诉诸法律(在古代中国,法律与刑罚几乎是同义词),就意味着双方将“撕破脸”,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欢而散。在强调教育和调解的社会中,人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孔子说:“我听人抱怨,也和大家一样,一定要做到没有抱怨。”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心中,存在着潜意识中对法律的不信任。
不信任法律,并不代表中国人不懂用法律。法律不能作为“根”,但可以作为“工具”。中国社会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内敛性特征,造成了千百年来以身份为骨架、以伦理为筋的社会框架。法律被剥夺了塑造自身价值的机会,而必须充当这个僵死僵硬的制度的奴仆,只为身份伦理秩序提供威慑力量,让日渐衰老的社会细胞勉强维持下去,不被新生细胞和外来细菌吞噬。 从先秦儒家的“礼治以国,以德治国”、西汉董仲舒的“大德小刑”到盛唐长孙无忌的“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南宋朱熹的“德礼政刑,始末有始有终”,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不过是一个单向单一政治体制模式所明确要求的社会维护工程”,8而这个工程的成果,就是建构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最完善的个人法律体系。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浩如烟海的法律,但都只是身份的附庸、道德的影子。
反观西方餐桌,宾客们都是矜持、歉意入座的绅士淑女。宴席不是吸收营养的行为,而是宾客们展示优雅修养的舞台。面对熟悉或陌生的客人,各种话题只是简单触及,不脸红、不倾诉。温柔友善就够了,不张扬的傲慢和外交辞令也必不可少。在这种“陌生人环境”中,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底细,什么事都要解释清楚,怕言辞不靠谱,必须签字盖章才算数。为此,善于普遍指导的法律规范应运而生,它们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平等、确定的标准,让甲先生在与陌生人乙先生交往时,仍能有效预见对方的行为,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于是,法治在西方有了滋生的土壤。
西方并非天生就具有吸纳法治的能力。根据历史学家、法学家梅因的研究成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其文化之初,社会的单位都是“家庭”而非个人,古代法律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身份特征。但自古罗马以来,商业文化和私法精神在地中海沿岸不断生根发芽,摆脱了复杂身份的契约关系在西欧社会生活中逐渐确立了地位。正如梅因在《古代法律》中所说:“一切进步社会的运动,至今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10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进步运动”,走向了法治和现代化。而中国由于农业文明的不成熟和过度发达,始终没有改变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以契约取代身份。 这还是需要人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把身份这个概念从体制里、从头脑里消除掉。
二
中国人办宴席讲究丰盛、排场。自隋唐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那里农产品丰富多样,水陆交通发达。宋代把物质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人奢侈的宴席习惯奠定了基础。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对各家酒楼的描写,就是当时中国大城市宴席消费发达的真实写照。现实中,即便生活拮据的人,办宴款待宾客也不会含糊。像全鱼、全鸭、猪肘这样的大菜,往往是上完十几道其他菜之后,才上来。其实,光是这几道大菜就足以盛满一桌。可以说,食客的胃里,一半在滋养着他们,另一半在毁灭着他们。 除了浪费物质,中国人还喜欢在酒桌上消磨时间:吃不完的菜肴、喝不完的酒,在酒桌上得以充分展示,这是建立在宾客们可以饮酒游戏、嬉闹、吟诗、开玩笑、亲近他人、喝得酩酊大醉的前提下,而真正花在吸收营养和享受美食上的时间,大概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中国人的菜单总是让西方人大吃一惊。因为中国人可以吃地球上一切能吃的东西:天上飞的,大雁、鸭子、蝗虫;地上爬的,果子狸、穿山甲、刺猬、蚂蚁;水里游的,鲟鱼、水蛇、甲鱼、河虾、螃蟹;还有各种水果、蔬菜、糕点。只要你能想到的,没有中国厨师做不出来的。这还只是从原料上讲。从烹饪风格上讲,中国有八大菜系,每个菜系都有自己的亚菜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小吃。
总之,我花了那么多篇幅和精力去描写中国人餐桌上的富丽堂皇,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在吃饭上讲究一种浪漫风格,即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中国人把吃饭看成是一种享受的艺术,一种炫耀礼仪的运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整个中国国家机器都是在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基调下运作的。这种性格的一部分想必是在酒桌上养成的:一方面,各级官员必须经常出席各种宴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挥发酒精、抚慰肚子上;另一方面,这种在酒桌上懒散、奢侈、随意、随意的作风必然会被带到公务中。此外,中国古代(甚至现在)的司法官员本身也很少接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他们首先是能写诗写文章、通晓儒家经典、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书法家。 至于实际工作,则以礼仪道德为主导,根本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程序,审判很大程度上依靠司法官员的“原判”。统治者并不关心法律的技术与原理,也不怎么在乎司法效率,他们认为只要懂得教化、善待人民,就能建立有序的伦理秩序。事实上,中国法律依靠的是“卡里斯玛”式的统治,其机会成本就是中国人失去了建立职业化官员制度和理性法律的机会。
这个机会最终被西方人所获得。马克斯·韦伯说:只有在西方才有理性意义上的国家。12西方人总是惊叹于中国餐桌上食物的丰富和多样,因为他们本身就习惯于信奉克制、理性、简练的处世哲学。西方人把最丰盛的宴席形容为七道菜的晚餐,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七道菜按顺序排列在桌子上是一种奢侈!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为后世贡献了光辉的人文财富(如哲学、悲剧、史诗等);而世俗世界的一切主要来自古罗马的建设(罗马帝国晚期,西方人的最高信仰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大帝确立为国教,这是上述讨论的一个重大例外)。古罗马在处世哲学上与斯巴达人相似,信奉严肃、朴素、纯粹的伦理规范。 这一理念渗透在当时发展起来的自然法思想中,使其也注重理性和合理性的价值。在黑暗的中世纪,自然法与基督教教义相融合,产生了以托马斯·阿奎拉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罗马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家主张“禁欲主义”,生活的精致和享受被认为是违背自然理性的行为。在对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中,“宗教禁欲主义”逐渐转变为“世俗禁欲主义”。在这种世俗化的宗教信条下,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勤劳、努力等美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重商主义风靡整个欧洲,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追求以最小的比较成本在对外贸易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使整个社会热衷于开源节流,提高制成品的生产效率,争取对其他国家尽可能多的贸易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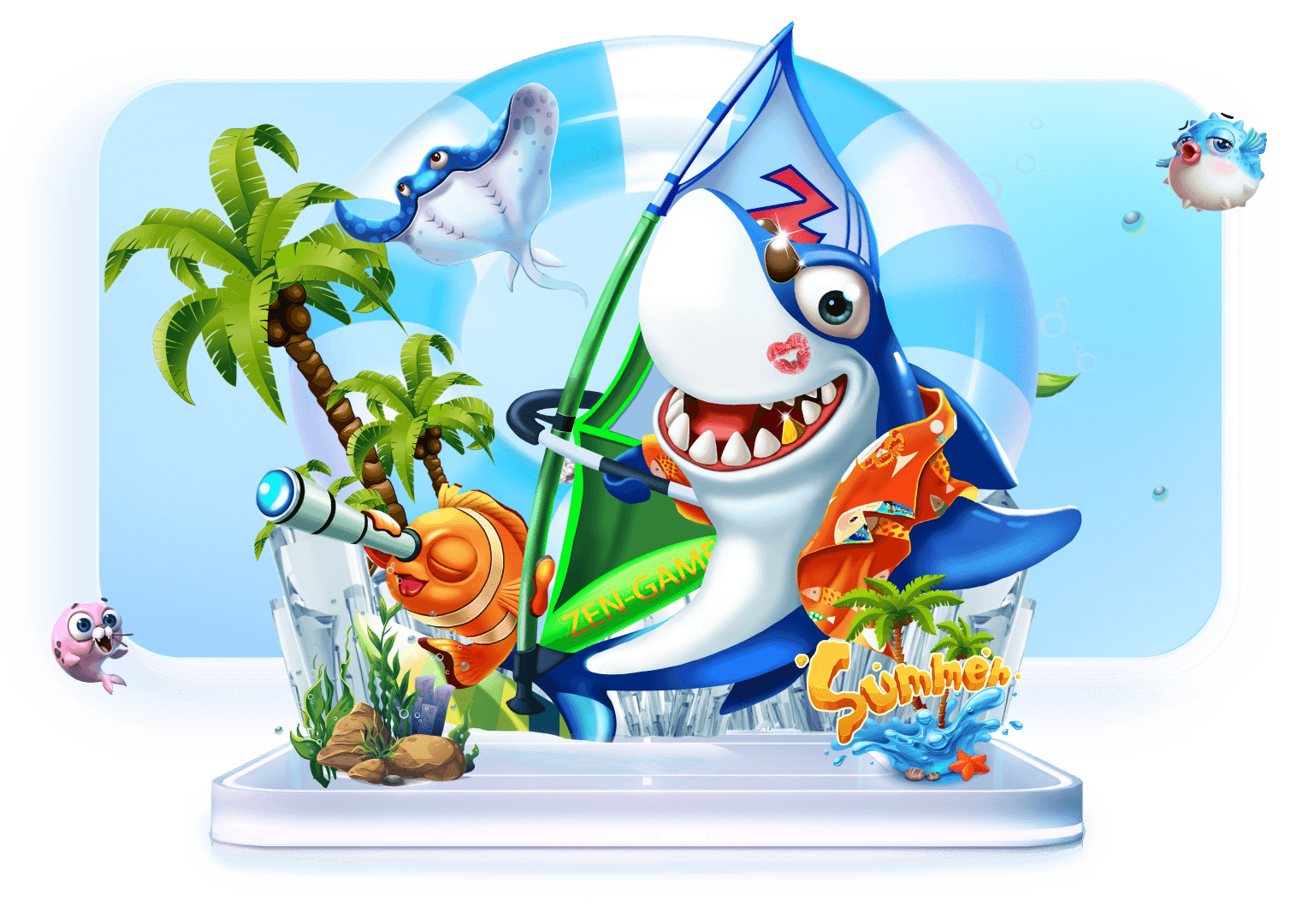
在西方历史的长河中,通过自然法→基督教→宗教改革→重商主义的思想脉络,理性理念与西方法律观念深深纠缠在一起。一方面,理性构成了西方法律的气质,贯穿于西方法律的三大支柱,即良法、程序正义和法律专业化: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提出了法治的两层含义,13成为西方治理模式的经典框架。西方社会以高超的立法技术、反映时代的需求,忠实地遵守法律,使法律“类似于一台可以预测的机器”;伴随着法治的建立,程序正义的理念与制度也在法治国家得以确立,理性化的诉讼制度使案件不受司法人员的意志和情感左右,司法的随意性大大降低; 最后,无论是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中世纪神权法学家、博洛尼亚学派的评论家,还是伦敦的律师和德国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西方历史上的法律职业者为法律的理性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理性国家的支柱。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当西方拥有了“类似于可以预测的机器的法律”、理性的诉讼制度和成熟的法律职业者阶层时,它就成为典型的“形式理性”制度,14从而完全排除了像中国这样的人格化治理。
三
中国人餐桌上最常用的餐具是筷子,有时还有酒杯和勺子,其余餐具一般都是公用的。因此,中国人难免会受到同桌人的影响,比如大汤匙和调料盘一起用,更有甚者,吃火锅时干脆把配菜和自己的筷子、公勺一起放进锅里搅拌。这样,每个人在餐桌上的行为都必须以观察别人的行为为基础,避免因餐具问题而发生冲突。不经意间,中国人表现出一种“集体主义”15的倾向,习惯性地先权衡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却逐渐淡化个人意志。集体主义带来的个人意志的淡化,也体现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夹菜”行为上。每个人都有为别人夹菜的“权利”,对方必须欣然接受并吃完,否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尤其是长辈为晚辈夹菜的时候。 即使对方不喜欢这道菜,也要含着眼泪吃下去,还要忍受端菜人满意的表情。如前所述,敬酒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受敬酒人的意志往往受餐桌气氛的影响。这也是集体主义的典型例子。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也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面。无论是历史上无数的集体惩罚、集体处决、种族灭绝,还是《红楼梦》中薛、王、贾、施四大家族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餐桌的“集体主义”也深刻地说明了这种文化。中国人吃饭时频繁交换餐具,间接唾液交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餐桌上有一人得了传染病,全桌人被传染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非典时期中国宴席的蛰伏,类似西餐的按人就餐方式的盛行,正是这种“集体主义”就餐方式的突然警醒和瞬间扩大。有人说非典时期餐桌上的分裂破坏了中国人的和谐观念。其实,这是一个逆向的逻辑错误。 正是因为中国人太过执着于“同一性”的群体观念,才使得原本难以统一的餐桌,千百年来始终保持不变。
正是因为中国人被困在“集体主义”这个牢笼里,只懂得为集体负责,不懂得为自己负责。只懂得服从集体、家庭的义务,却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作为个体,他们往往缺乏“个人主义”的概念。个人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是不是中国思想教育所批判的自私自利的同义词?这其实是根植于中国思维的狭隘误解。要提炼出这个词的准确概念,必须回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凡是吃西餐的中国人,都会被餐桌上琳琅满目的餐具所吸引。一顿正式的西餐,餐具一般包括:大盘、小盘、深盘、浅盘、沙拉叉、肉叉、面包刀、锯齿刀、汤匙、开胃酒杯、红酒杯等。如果遇到蜗牛等形状特殊的食物,贝壳夹、小肉叉等餐具就更多了。所有餐具都整齐地排成一排,仿佛是私有财产,食物直接分份放在盘子或杯子里。整个就餐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之间不需要交换任何餐具或食物。20世纪以来颇为流行的快餐,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所有食物都单独包装,分给每个人,吃完之后,一切由你决定。
法治国家的西方人在个人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随心所欲。这里所谓的“随心所欲”,并不是说不受法律约束而任意行事,而是指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独立的存在和价值,不仅要保持这种价值,而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自主人格的主张。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发达的海上贸易就使地中海地区的商品经济传播开来,商品经济又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平等权利法律关系的发展。既大大促进了人权的发展,也为公民的自主和个性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城市文明的繁荣和私法的发展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基础。11世纪地中海贸易的兴起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导致西欧市民社会的出现,使个人再一次被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位置。个人主义的生长贯穿了西方的整个发展史。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重视个人主义的地方,私法就得到发展。因此,西方社会的法律精神是个人主义的私法精神。而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长期奉行集体主义和道德伦理,私法精神难以确立,个人主义无法生根发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法律首先是“公”,它总是借助权力以高不可攀的地位来到我们面前;它总是与“刑”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历代的帝制法典基本被刑法所垄断,其他法律法规只占非常有限的部分。总之,西方法律文化是私法文化、权利文化;中国法律文化是公法文化、刑民文化。16
四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一幅从东方到西方的人法图景:
(中国)(西方)

内部:身份契约
气质:浪漫、理性
标准:刑事权利
这是中西方法律理念的比较。这里所谓的“理念”其实是西方的舶来品,译自西班牙语“Idea”。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要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最实在的存在,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它具有普遍性和独立性,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17这里我着重从饮食的角度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进而概括出法律理念的三位一体:内在、气质、规范。所谓法律的内在性,是指法律的内容实体所散发出的知识取向,在中国表现为身份,在西方表现为契约;所谓法律的气质,是指法律作为生命体所展现出的性格和气质,在中国表现为浪漫,在西方表现为理性; 所谓法律本位,是指法律设计的出发点和基本价值,在中国表现为惩罚,在西方表现为权利。这三者犹如人的身体、精神、灵魂,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同构的法律概念,将中西方文化区分开来。
反之,则是道之运动,任何差异都无法阻止巧合的发生。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萌芽之时,所有民族都趋向于类似发展。由于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东西方的方法和理念逐渐渐行渐远,将一个思想大陆分裂为两端。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客观因素逐渐被人们克服,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交流日趋繁荣。因此,上图也可看作是东西方方法和理念理想和谐的流程图。然而,中国法律理念的路径,究竟是如箭头所示采取兼收并蓄、向西方方法和理念靠拢的路径,还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契合呢?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学者对两大理念历史传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找到差异的原因和巧合的依据。 两千多年前,两个法系概念还在襁褓时就被创世主分开,当重逢之日到来时,他们要仔细端详对方的容貌和身影,当发现彼此拥有相同的血脉,便会发生融合。
后记
这篇作文的灵感来源于课堂上的一点小感悟。当时我正在讲授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思考,一个调皮的学生大喊“她饿了”抗议我的拖延。在下节课中,我即兴编撰了一篇关于中西法律传统与饮食文化对比的分析讨论,以刺激这个学生的饥饿感,并给予她小小的惩罚。然而,课后她却很恭敬地把笔记交给我检查。多亏了这篇笔记,我这几天修改了内容,查找了一些理论资料,补充了几点,整理成了一篇拙文。只希望读者不要鄙视它的拙劣,而是会心甘情愿地阅读,以此砖吸引更多的金玉。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听说费孝通先生去世了。虽然我和他没有私人关系,但费先生一直是我敬佩的学者。我对法律社会学的很多看法,包括本文的一些想法,都是在费先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里,我谨向费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他是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作者注
武昌珞珈山乙酉立夏



